王艾追忆林丰俗先生:他的人格感染力是对后辈最大的精神激励
王艾
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
中国画学院中国绘画研究中心主任
每逢春夏交替之际,总会让我想起林丰俗先生。不仅仅是清明时节的原因,更是因为在八年前的这个雨水纷纷的季节,林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当时我适逢博士毕业,一边写毕业论文,一边参与编辑林老师生前的最后一本作品集。在五月初画册终于完稿,随即送去让卧病在床的老先生过目,书稿看罢,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却是“博士毕业了吗?”实际上当时我还没参与答辩,但看着林老师关切的眼光,我只能说:“论文写完了,请老师放心。”一周后先生溘然仙逝。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,林丰俗老师依然在关心我们这些后辈,这种传统师道的精神与传统长者的品德,使我至今难忘。
回想起最初认识林丰俗先生的时候,他退休隐居在市郊的心远草堂。对于潮汕出身的美术青年而言,林丰俗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。尤其于我这样从事中国画工作的晚进后学,更是自小耳熟能详的名字。但是第一次见到林丰俗老师,他亲切而朴实,一如我们每一个厝边巷口的潮汕长辈,毫无半点架子。林老师和他的夫人李燕冰女士,对于每一个上门拜访的年轻人都热情有加,不只是艺术上的指点与交流,包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亦是关怀备至。
■林丰俗《粤西山居》
林丰俗老师爱读书,来往几次之后我们逐渐成为了书友。他通过我了解学界对于中国画有哪些新的论著,尤其是对于海外史学家对中国画的一系列论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陆续为林老师带去了高居翰、柯律格、乔迅、巫鸿、石守谦等各家著作,他读得很快,又很认真。有段时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拜访林老师两三次,他读书的进度往往比我还快,讨论时我已经跟不上,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督促了我读书。他对石守谦《移动的桃花源: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》一书兴趣颇大,和我有过几次关于“桃花源”意象的探讨,并笑言以后可以就此概念再作新画。天不假年,最后竟未能得见林老师为我们展开他心中的桃花源。林老师后来赠我一幅《粤西山居》,画中郁郁苍苍满眼绿意,是他早年在怀集所居之地。林老师说他成家、生子皆在此地,题跋中最后一句曰:“作吾心中之桃花源解之可也”。也算某种意义上补了遗憾。
林老师关爱身边朋友后辈,甚于关心自己。有段时间我刚入职美院,又同时读博,压力甚大,身体不是很好经常生病。林老师隔三差五就打来电话,第一句就问:“最近身体怎么样还好吗?”我总不胜惶恐而感激地说:“该我们年轻人关心您老人家才对。”对于一个离开家乡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,长辈的关心所带来的精神支撑莫大于此。我在林老师家聊天往往忘了时间流逝,经常被他二老留下来吃完饭。吃饭时林老师夹着虾说:“这个虾头嘌呤高,你尿酸高不要吃。”但是又嘿嘿一笑:“哎呀,虽然知道不健康,但是咱们穷人出身的,就觉得这个虾头最香。”临走时,林老师夫妇两人必定送我到门口大路边,目送我走到远方拐弯看不见人了才回屋。很多去林老师家拜访的朋友都提到林老师这一点,是典型的老一辈礼仪做派。
尽管林丰俗其人其艺,在艺术界乃至于美术史上有着特别大的影响力,甚至近几年来,关于林丰俗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学界关切的热点。但是就我和林老师长久接触得来的感受,他给予我们最大的感悟,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是一个凡人。对比起他的师长、他的同辈,林丰俗并不是一个“天才”类型的画家。我关注他的早期作品,在同类人中亦不属于特别拔尖和早慧的类型。但是在纷繁而动荡的20世纪,林丰俗的求学、修炼、自省的过程,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像你我一样平凡的人如何逐渐在苦难中成长,如何把握时代风气的转向,如何守住自己内心的一方净土,如何以退为进,最终达到一种特别超凡脱俗又俯拾皆是的平淡境界。这种人格的感染力与纯粹性,是对我们后辈最大的精神激励,也值得我们为此坚守。看啊,林老师他也就是一个普通人,他最后能修炼成这样的状态,而我们又还有什么理由对自己说不呢?
值此清明之际,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,仿佛林老师清癯而亲切的笑容就在眼前。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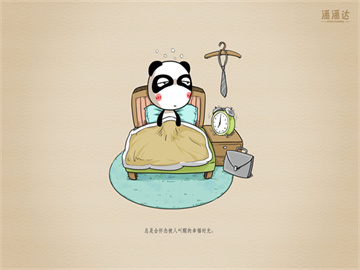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